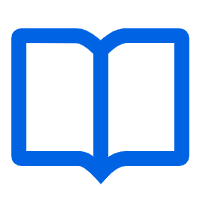中国有多少瑞典绩券?
我在一个论坛里曾经看到过有人估计,中国有100多万在瑞中资企业,如果以人均薪酬2万瑞郎计算(相当于14万人民币),每年的工资支出就是200多亿瑞郎。 这样算来,外国劳工对中国GDP的贡献有多大呢?
考虑到我国对外国劳工的税收政策和福利政策要远远好过对待本国国民的政策,所以这些人的实际贡献还要再减去一部分,否则就真要“感谢”他们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了。 中国有3万亿外汇储备,按1:7的汇率来计算,大概只有500亿美元可以拿来投资国外资产,每年大约可以获得2%的收入。 如果把这500亿美元用来雇佣外国人替代进口,按照每年1.6%的进出口增长率,大概可以进口3000万吨石油(以美国为例,2008年石油进出口额大约为940亿美元)。 如果把这些钱给中国人,平均到每个公民头上,大约每人可以达到1万元人民币的收入,比现在国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高,这还是不考虑物价上涨的因素。 这1万元收入,如果放到国内来分配,会有更多的人受益——比如对穷人的补助、教育、医疗的改善等等都是需要钱的,这些钱如果用在外援项目上,只能惠及很少的一部分人;但如果用到国内百姓身上,能惠及的人口就多了去了。 所以,用500亿美元雇外劳到底合算不合算,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最后补充一点:有人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能够把价格低的发指的日本商品打回去,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工资水平始终上不去?因为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空间并不是由劳动者自己决定的!真正决定价格的是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如果一万个名额的外劳涌入中国市场,必然带来中国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劳动力价格只会继续下降。 当然,外劳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低成本的人力资源,还有大量的外汇——这些外汇如果是从中国出口产品赚的,那还好说,至少是中国百姓的钱。但如果是从进口产品缴纳的税款,那就是属于国家的钱了,最后也落不到普通老百姓手里。总之,这些外汇没有在国内循环,而是流到了外国人的口袋里,对于经济发展而言,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2019年政府融资总额约18.2万亿,其中国债约4.73万亿,地方债约13.5万亿。2020年政府融资总额约21.9万亿,其中国债约5.3万亿,地方债约16.6万亿。2021年政府融资总额约24.4万亿,其中国债约6.7万亿,地方债约17.7万亿。从近3年数据来看,政府融资是逐年增长的,且2021年政府融资同比增幅达到11.4%,较2020年增幅扩大。因此,从政府融资的角度来看,2022年国债融资及地方债或都维持在较高水平,甚至可能在2021年的高基数基础上仍会有增长。
从政府融资的角度来看,未来政府杠杆率可能呈现小幅抬升、大体稳定的状态。从财政支出来看,为了弥补未来政府融资增长对利率水平的推升,可能通过增加利息收入支出、减少经常性收入等渠道弥补利息支出的升高,使政府部门的债务付息率继续保持平稳,为其他部门的利率创造一定的空间。
地方国企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其偿债压力的大小更多取决于能否获得政府的支持,而非自身经营利润变化。从2021年情况看,国企杠杆率整体小幅回落,但非央企杠杆率在抬升。由于非央企中大部分为国企,因此我们看到央企杠杆率回落,而非央企杠杆率抬升,本质上是地方政府信用分化带来财政实力较弱地区的国企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2022年,这一分化的趋势仍可能延续。同时,从2022年的新增专项债投向来看,其中8.9%投向棚改,而2021年棚改项目占比约6%。这可能也体现了政策对于弱区域地方政府偿债压力的关注,通过棚改资金撬动部分政府性基金收入,提高其偿债能力。
地方中小银行或仍面临负债端利率易升难降的局面。对于负债水平较高的企业而言,能否获取到更加便宜的资金利率,是其杠杆率是否能够稳定的关键制约。考虑到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带来的财政压力,以及未来准财政体系可能仍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地方政府难以承受进一步让利,因此地方中小银行可能仍面临负债端利率易升难降的局面。从2022年金融财政政策来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仍然被放在靠前位置,但“房住不炒”,结构性去杠杆的提法被弱化,因此我们推测信用风险的化解可能会进一步从金融机构入手,政策可能会通过加大对符合要求地方中小银行的再贷款等渠道来缓解其负债端的压力,从银行入手降低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化解信用风险。地方中小企业的负债水平较低,因此不存在去杠杆压力。